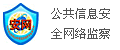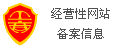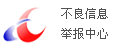第一次看戏
那是我第一次看戏。以前也许是看过戏的,我曾认真地从记忆深处打捞,有一次把我的手都打捞疼了,还是渺无踪迹。无论对于群体,还是个人;也无论是记忆本身的故障,还是人为的遮蔽,遗忘了的,便可视为不存在,这是很无奈的事情。这么一来,我便有堂皇的理由,把自己第一次看戏的时间确定为五岁那年夏天。
没有戏台,给打麦场的中间搭一顶帐篷,就是戏台了。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那种帐篷。现在常见的帐篷,在我看来是很奢侈的,人住在里面,冬天保暖,隔绝风雪的侵袭,夏天凉爽,把阳光风雨挡在外面。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拥有这么一顶帐篷,一直是我久远不灭的梦想。四根杂木椽子四角竖起来,用破旧的麻绳链住椽头,把几张破旧的芦席搭上去,这就是帐篷了,这就是戏台了。阳光射进来,帐篷里一半有阴凉,一半阳光灿烂。我在最前面抢了一个屁股大的地盘。那时候,我的屁股很小。观众都席地而坐。好长时间没下雨,黄土地皮裂开了,满地都是半寸厚的浮土。浮土很细,白面一样细,屁股坐上去,温吞吞的,抓在手里,也温吞吞的,用手一摸就像抚摸乳房时的那种温馨。偶尔有人站起来,便会带起大团的土雾,许多人都会被笼罩得面目模糊。当即,嘴里的呸呸声,呵斥声,咒骂声,便盖过了戏台上唱戏的声音。戏台上那个钉鞋的人是我表哥。他是一个赤脚医生,给我打过针的,他搞得我屁股蛋子很疼。我很怕他,也很反感他。他就在我的当面,离我最多一步远。他的脸上涂满了油彩。他蹲在帐篷边,那里阳光灿烂,他脸上的油彩消融了,与汗水搅和在一起,像把一颗熟透的西瓜砸在了脸上。他一只手拿了一根半尺长的木头橛,在地上棒棒乱敲。他身后是李奶奶和李铁梅。李奶奶是我邻居王强他妈,李铁梅是王强他大姐。王强他大姐拖腔叫道:奶奶——王强他妈居然也拖着长腔答应了。我急了,我说错了,叫妈哩。我的叫声可能是比较急切,传来一片哄笑声。钉鞋的表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攥紧手里的木头撅,作势要敲我的脑袋。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认定大人是不讲理的,明明叫错了嘛,人咋能把自己的亲妈叫奶奶呢。我在木头撅的当面威胁下,没有做任务争辩。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我遇到不讲理的人,一般都保持高度的沉默。李玉和出来了,他是我表叔,他挂在身上的铁链子是我家捡狗用的,手中的红灯是我家在队里晚上分粮时途中照明用的马灯。我喜欢表叔,虽然,他脸上涂满了油彩,身上挂着拴狗的铁链子,我还是喜欢他。
过了几天,我去农田工地玩。表叔脸上的油彩没了,身上的铁链没了,手中红灯也没了。他肩挑一副很大的柳条筐,筐里装满土粪,扁担咯咯吱吱,粪筐忽忽悠悠,他喘着粗气,嘴里还咿咿呀呀。据说,马上还要演出的。王强他妈和他姐都在工地上,王强他姐把王强他妈叫妈,我心里有些愤愤然:我明明是对的嘛。我更反感表哥了,更对那些嘲笑我的大人不满了。王强他姐叫妈时,声音比叫奶奶好听多了:妈——平声出去,中间拐一个溜溜的弯儿,再平声结束。表哥不再当赤脚医生了,他被县剧工团抽去专门演戏。我反感的人从我眼前终于消失了。几年后,他回来了,赤脚医生已有别人当了。他和我表叔,和王强他妈他姐差不多每天都在一块农田里劳动。下了戏台,抹去脸上油彩后,他们的脸和大家一样,都是汗水和尘埃。 (通讯员 辛恒卫)
版权声明
本网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注:凡注明“来源:XXX(非陕西城乡劳动就业网 sxcxldjy.com)”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邮箱:782481785@qq.com】
推荐
-
27 / 11月
青春绘华章 社保暖民心——宝鸡市养老保险经办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 -
21 / 11月
三秦匠心绽邕城 劳务品牌亮全国——陕西特色劳务品牌闪耀第三届全国劳务协作盛会 -
11 / 11月
川陕家人:把陕南山水鲜气,端进西安的烟火堂屋 (一) -
21 / 10月
西安市人社局局长廉宏伟一行调研新山海源集团,共商发展大计 -
20 / 10月
全省依法行政和劳动保障监察培训暨治理欠薪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安康成功举办 -
16 / 10月
金秋聚宝鸡,劳务品牌展新辉 ——2025 陕西省劳务品牌交流活动启动 -
23 / 09月
陕西代表团夺得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两银一铜 -
20 / 09月
陕西 116 名选手征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特色展馆人气爆棚 -
20 / 09月
技耀中原,能汇九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幕 -
20 / 09月
陕西 116 名选手出征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
热榜
标签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