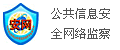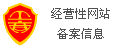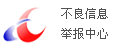我还未走远的记忆 (之一)
(作者:李崇文)
清晨,昨夜——场雨,让整整铺着一层尘土的路愈加泥泞不堪,忙了月数天的人们难得地美美地睡着,脸上虽有疲惫之色,但不经意间会露出笑来,因为收成很好。罕见地,公鸡呆在架上没有打鸣,狗也趴在窝里没有像往常一样,呼朋引伴,满村乱蹿。
伍哥猫着腰,光着脚走在前面,不时向跟在后面的我招手示意。他胸前挂着书包,我知道里面的几本书都快成了“油饼”,还有的就是弹弓、弹球、三角和四角等玩意。而我斜背书包,双手提着裤子,塑料凉鞋在泥水里打着出溜,有时发出扑嗤声,便招来伍哥一顿白眼。
我俩昨晚分手前就商量好了,今早早早起来,到村北头姜家偷摘桑椹。
整个村只有姜家有桑树,而且是两棵,一棵结得是红桑椹,一棵结得是白桑椹。红桑椹树树高冠大,几乎把姜家后院罩了个大半。白桑椹树在红桑椹树西北上,像红桑椹树的女儿,娇小多姿。红桑椹果大汁多、白桑椹晶莹洁白,但就一个字“甜”。那时学校门口也有卖的,五分钱一洋瓷缸,一放学,手里有零花钱的学生就把卖桑果的围了个满满当当,一买到手,迫不及待地的抓几颗塞到嘴里,有意嚼得汁水四溢,还四下里看看,最后把手随意地在屁股上抹抹,那补好的两块蓝黑布片更显光滑。
有一次,伍哥攥着姑婆给的钱买了一缸子,等我出来一起吃。我俩蹲在学校大门左边,写有“严肃活泼”的墙底下吃,不一时缸子见了底,伍哥意犹未尽地扎巴着嘴说“没有姜家的甜”。
此时,姜家人还没起来,夫妻两人带着个哑巴男孩,男孩叫“锋”,和我大小一般,没上学。伍哥撅起屁股,慢慢爬到后院土墙根,从裂开的缝隙里观察着,接着他把书包摘下来递给我,自已像个蛤蟆似得往上爬,右脚向上一跨,就骑在了墙头。一手张着土布褂子,一手快速地攀折着桑椹,枝枝叶叶的。我在下面仰着头,张开书包,褂子满了就倒向书包。“满了”,我压低嗓音说,“我再摘一点,那个枝条上的红得很”,伍哥有些贪心。我担忧地看着他竟然试图站在墙上,去勾差一扫把就能够到的桑条,心不禁跳得嘭嘭嘭。“叭嗒”,一大块土圪塔掉落到院子里,“伍,你狗什的可来了,还没完没了,看我收拾你个崽娃子”,男主人羊娃叔一嗓子吓得伍哥摔了下来,我盯着他看,好么前几次竟然不叫上我。伍哥眼一翻说“还看啥哩,你个瓷棰,赶紧跑”,两个人泥里水里一阵跑,嘴里“哈哈哈”地笑个不停……
伍哥边走边说“一会到学校大门口,你把我的三角拆开,这样一折,我给里面装桑果,红的卖三分、白的二分钱”。我看看他,看看桑果,满是不舍。“好啦好啦,给你留5分钱的,要红的、白的你随便,咋样?”,我咧开嘴笑了。由于卖得便宜,不一会就卖玩了,我捧着留给我的只是吃,不操心卖了多少钱。伍哥点数着分分钱,也不管上面沾着桑果汁就装进了上衣口袋,扣上扣子,还压了压对我说“钱放我这,星期天咱俩带上小人书到新华书店摆个摊,用这钱买一套《西游记》,如果还有余再买几本《杨家将》”“唔、唔、行”我嘴里含糊不清地应道。
伍哥是我的表哥,大我五六岁,那时有十五六岁,最是淘气,待我很是不错,掏鸟窝、捉鱼虾,鱼塘、野地、渠岸能玩的地方,无论春夏秋冬都留下了一高一低两个人的身影。他是他家唯一的男孩,上面四个姐,还有一个妹。所以,我表叔虽然三天两地又打又骂,但在我姑婆的避护下,还是在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就犹如奇迹。
我喜欢看小人书,也攒了二、三十本,细心地用木头箱子装在一起。伍哥说,咱还得赶个早,找个好位置,不然太阳出来热得不行,另外到时候我负责叫人,你给咱守住摊子,対了,我叫你婶给咱烙两张油馍有葱花的,你带上水壸,咋样?我说行。
县城不大,主街呈“十”字形,南北短、东西长,一逢集,人多得就走不动。那时仅留的一段南城墙。在风吹、雨淋和日晒中所剩下多,更多的是男孩子玩耍的地方,他们爬上去又滑下来,乐此不疲,许多地方磨出光溜溜的滑道。新华书店在东街,坐北朝南,有三间门脸。红色门框中嵌着平板玻璃,透过去能看到一柜一柜的书。书店旁边有棵老杨树,有二十多米高,周边用砖箍了个圆形台台。我们就在树下铺上塑料纸,把书一本一本摆好,日头起来了,书摊刚好在树荫下。
正吃馍馍时,书店门开了,我赶紧说“伍哥,快去买书”,“急啥,人家还要打扫卫生,等会儿,让我把这口馍一吃”,五哥很是拿稳。街上行人慢慢多了,有几个还带着孩子,“我去买书,你可把摊子看好,记得薄的1分、厚的2分”伍哥说着就进了书店。等他出来,书摊边已有几个娃子坐在地上看书了,五哥一边把刚买的《杨家将》递给我叫摆上,一边问“钱收了没有”,我张开手给他看了看,说“差不多有两毛了”。伍哥把钱装进口袋里说“我给咱收着,最后算账”。
太阳升到了头顶,伍哥拿着水壶跑到书店后门去接了些凉水回来,问我喝不,我头都没抬说“不喝”,因为正看到杨七郎被箭射死了。不知啥时候,伍哥又不见了,四处望望,见他捂着肚子从路对面公厕出来,“不行了,拉肚子,可能凉水喝多了”,看他难受的样子,我说“咱回吧,到医疗站买些四环素”,“好吧,把书摊一收,呀,书咋少了好几本,杨家将也少了两本”,伍哥再把钱点了点,不到一块五,“赔了,杨家将一本要两毛五哩。”
多年以后,我仍记得那个让人沮丧的下午。 两人一改来时的高昂情绪,快到村里,伍哥拉住我说“是这,我给你补五毛,光看书守不住摊子,做不了生意,好好去念书吧”。一晃快四十年了,五哥的话得到了应验,我一步步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是村子同年十二个孩子里把书念出来的两个人之一;而伍哥终不再上学,靠着精明和踏实,盖了新房,娶妻生子,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这就是我还未走远的孩童时代的记忆。
版权声明
本网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注:凡注明“来源:XXX(非陕西城乡劳动就业网 sxcxldjy.com)”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邮箱:782481785@qq.com】
推荐
-
27 / 11月
青春绘华章 社保暖民心——宝鸡市养老保险经办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 -
21 / 11月
三秦匠心绽邕城 劳务品牌亮全国——陕西特色劳务品牌闪耀第三届全国劳务协作盛会 -
11 / 11月
川陕家人:把陕南山水鲜气,端进西安的烟火堂屋 (一) -
21 / 10月
西安市人社局局长廉宏伟一行调研新山海源集团,共商发展大计 -
20 / 10月
全省依法行政和劳动保障监察培训暨治理欠薪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安康成功举办 -
16 / 10月
金秋聚宝鸡,劳务品牌展新辉 ——2025 陕西省劳务品牌交流活动启动 -
23 / 09月
陕西代表团夺得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两银一铜 -
20 / 09月
陕西 116 名选手征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特色展馆人气爆棚 -
20 / 09月
技耀中原,能汇九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幕 -
20 / 09月
陕西 116 名选手出征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
热榜
标签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