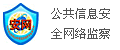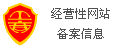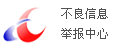我还未走远的记忆 (之二)
(作者:李崇文)
一九八一年中秋节过后的一天,老屋前的土堆上,我左手拿着半块硬锅盔,右手攥着一把炒熟的玉米豆,伸长脖子向东边望,和往常一样。嘻嘻哈哈的欢笑声老远就传了过来,我知道学生放学了。他们三五成群,说个没完没了,还看见一个男娃前面跑,一个女娃抡着书包在后面追,打闹嬉笑。我蹲下来,双手撑着脸,很是羡慕,直到路上恢复了平静。
“文,吃饭了”,母亲喊我。回到家,端起玉米糁糁,看了看旁边的酸黄菜,对母亲说“妈,我也想上学”
“过两天逢集,捉个猪娃养着,明年九月前卖了,就送你上学。”,母亲笃定地对我说道,像似早就打算好了。从那天起,我就开始扳着指头,计算赶集的日子。
牲口市场挨着县城边边,紧北面就是南环路,有近二三十亩地的样子,牛、马、骡、驴、猪、羊、狗及家禽等被划出不同区域买卖。逢集那天,吃罢早饭,父亲下地出工,母亲拿着蛇皮袋子,去了牲口市场,并嘱咐我看好妹妹,安安在家等着。兄妹俩从开始兴奋得猜买回来的是黑猪、白猪还是花猪,到最后一人靠着一边门框,打起渴睡。“文,撕一抱麦秸来”,母亲的突然一声呼唤让我一激灵。抱来的麦秸被放在院庭,母亲用火柴点燃,又从蛇皮袋取出猪娃,提着后腿在麦秸的烟火里燎了几个来回。“一定能长成大猪”,母亲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露出满是希望的笑,妹妹也一旁拍着手跳着。
第二年收完玉米,我穿上母亲用车轮胎做底的新步鞋,挎着母亲缝的布兜兜,拿上小板凳,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而且这一念就是十六年。
小学里有一位李老师是我们村的,也是我五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颇受人尊敬。那年收麦,我家就在场院北面,看着李老师悠悠地从村东头走过来,母亲倒了杯水,让我搬来唯一的靠背椅,招呼李老师说“李先生,快坐”,又很是期望地问,“你看我娃考学咋样?”,李老师喝了口水,看看母亲,又看看我,不紧不慢地说“嗯,畔畔上哩”。事后,母亲盯着我说“文,妈不识字,你要争口气。你爸说了你上到哪就供到哪”,我回应到“嗯”。
小学二、三年级时,土地开始承包到户,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我家有六亩,人均一亩半,母亲从此一心扑到了土地上,小麦、玉米、棉花、黄豆、油菜仔,能种都种,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岁月。家门口有两块大小相近的青石,父亲告诉我东边的是上马石,西边的是门蹲石,有好多年头了。不记得多少次了,放学回来,大人们还在地里忙活,就趴在上马石上面写作业,常常就睡着了,忘记身下的青石是凉是热。
小学、初中、高中,先前一起上学的同龄伙伴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我和一个姜姓同年。一度时间,我俩相伴着一起上学,彼此鼓劲打气,后来他学政法去了公安,我学中文进了社保。
那时候上学,不用大人叫,更没有车接车送,自已起来,竹笼里拿个锅盔或蒸馍,不用花钱买早点。放学放假也不补啥课,上什么兴趣班,一回来就帮家里做各种活计,扫地烧锅、喂鸡看娃、锄草打药、收麦摘花(棉花),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又从冬到春……
我高中读了五年,补习了两年,三进高考考场。当时,把七月高考称为“黑色789”;学校里戏称补习生为高四、高五甚至高六。我就知道有一个女学生补了五年,真不知道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高四的失利让我闭门不出一个多月,时常望着床上成堆的书,成摞的资料,总是狠不下心捆起来送到废品回收站。家里也不再像往日般热闹欢快,家里人出出进进悄没声息,说话也低声细语,气氛说不出的压抑。父母有心让我出门转转,可又担心我想不开出个啥事,我能感受到他们在背后望我时那种说不出的担忧。那段日子,看着家人和我一起煎熬,心里真不是个滋味。眼看着九月近了,是该做出决定了,我想。
就在开学的最后一天,我走出房门来到后院,母亲正从鸡舍走出来,提着铁皮壶准备接水。就在后院的那棵大杨树下,我跪下来哽着对母亲说“妈,我还想再考一次”。母亲扔下壶,一把拉起我说“学费都准备好了”,迅速转过身去取钱,我分明地看到母亲用衣襟展了好几次眼,这个场景多少年后不止一次地从记忆里走出来。
第二年,考后估了分,觉得比上年有把握,三天全身心投入考试,我瘦了三四斤,一家人也都紧张地期待着。 八月底的一天,我和父亲、母亲在地里栽蒜,我在前面拉着“幸福犁”,带着湿气的泥土在犁两侧翻滚,土地上犁出道道沟渠,父亲和母亲将破开的蒜瓣一颗一颗摆进去,再覆上土就要完工。
“爸、妈、哥,考上了”,地头远远的传来呼喊声,就看见在家里做饭的妹妹向我们跑来。那一刻,喜悦笑的容终于在家人的脸上展现出来,映着阳光显得那么舒心灿烂。我俯下身,抓了两把泥土,深深地攥了又攥,长长呼出一口气,抬头仰望,天空是如此澄净美丽,身心从来没有过地轻松,一如天空里随风舒卷的云朵。
那一年,家里种了洋葱,亩产近六千斤,市场上价也不错,收成很好。
版权声明
本网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注:凡注明“来源:XXX(非陕西城乡劳动就业网 sxcxldjy.com)”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邮箱:782481785@qq.com】
推荐
-
27 / 11月
青春绘华章 社保暖民心——宝鸡市养老保险经办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 -
21 / 11月
三秦匠心绽邕城 劳务品牌亮全国——陕西特色劳务品牌闪耀第三届全国劳务协作盛会 -
11 / 11月
川陕家人:把陕南山水鲜气,端进西安的烟火堂屋 (一) -
21 / 10月
西安市人社局局长廉宏伟一行调研新山海源集团,共商发展大计 -
20 / 10月
全省依法行政和劳动保障监察培训暨治理欠薪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安康成功举办 -
16 / 10月
金秋聚宝鸡,劳务品牌展新辉 ——2025 陕西省劳务品牌交流活动启动 -
23 / 09月
陕西代表团夺得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两银一铜 -
20 / 09月
陕西 116 名选手征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特色展馆人气爆棚 -
20 / 09月
技耀中原,能汇九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幕 -
20 / 09月
陕西 116 名选手出征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
热榜
标签
关注我们